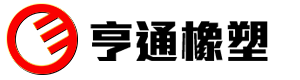milan体育app下载:88-90集丨洪江纺织厂回忆录——《巫水河畔的经纬岁月
milan体育app官网:
以个人笔触回溯洪纺从初创到谢幕的壮阔历程,不定期连载,欢迎微信留言,共温一代人的热血与柔情。
1978年建厂的洪纺,在曲折中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到2000年时,它已是湖南省除“八大棉”之外,中型纺织企业里的佼佼者——谁曾想,转年的2001年,竟成了它命运里一波三折的“渡劫之年”。
这一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国企改革也迈入“深水区”。对众多老厂子而言,“转换机制”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成了必须跨的坎。洪纺当时也在四处寻出路,最盼的便是“政策性破产”这根救命稻草。厂里专门给职工们宣传其中的好处:若能拿到这个名额,银行贷款便能一笔核销,企业可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与人竞争。自2000年起,他们便往上打报告,一门心思想挤进“政策性破产”的笼子,那一段时间,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大家精益求精地核对申请材料,总觉得“这事儿成了,厂子就有救了”。
可天不遂人愿,形势比人强。政策性破产需政府拨款,名额更是僧多粥少。当年湖南省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将仅有的名额给了省内最大的纺织企业。洪纺的申请如同泥牛入海,连个回音都没有。可“破产”二字,早已像风一样刮遍厂区每个角落。职工们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车间里、食堂里,到处都是窃窃私语:“怎么回事?厂子不是一直好好的吗?”“前些年还在说‘不断壮大’,怎么突然就‘资不抵债’了?”更有人红着眼质问:“我们的血汗钱到底去哪了?莫不是被人中饱私囊了?”那些天,连走路都能察觉大家心里的火气,空气里像掺了火药,一点就着。
疑惑渐渐酿成怨气。从五月份开始,大家先是三三两两在车间角落窃窃私语,声音压得极低,眼神里却满是不满;后来有人忍无可忍,公开骂娘,话里带着哭腔,念叨着“一家老小都指望这厂子”;再往后,从几个人聚在厂部门口据理力争,到几十号人堵着办公楼讨说法;最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关了机器停产,一群人拉着横幅上街,走到区政府门口便坐下了,放话“不给说法就不起来”。生产停了好几次,机器一停,整个厂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得人心里发慌,一度彻底失控。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节骨眼上,厂里一位主要领导又出事被查——消息传来,厂里瞬间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音,接着便是更大的混乱,真是应了那句“船迟又遇打头风”。
区里见状,急如星火,当天就派了人来。很快,“洪纺维稳工作组”的牌子便挂在了厂部办公室,由区政协工委主任任希平任组长,区经贸局局长印吉成任副组长。与此同时,厂领导班子也迎来调整:安排李建来接任公司CEO(董事长由印吉成兼任),企业名字也改成了“洪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宣布消息那天,李建来站在台上,望着台下几百双满怀期待的眼睛,手心全是汗。
那段时间,工作组的人与他们同甘共苦,一起泡在厂里。任希平主任每天都扎进车间,跟老工人拉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机器旁,把账本摊在膝盖上,条分缕析地给大家解释“钱花在了哪里”,声音哑了就含块润喉糖,天黑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印吉成局长东奔西跑协调事务,一会儿去银行询问情况,一会儿又去仓库查看库存,生怕生产断了链,鬓角的白头发仿佛都多了几根。李建来则从早到晚守在办公的地方,门始终开着,职工谁有疑问,随时随地都能来谈,有时半夜还有人敲门,他也起身跟对方聊,常常聊到东方发白。慢慢地,职工们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些,停摆的机器又嗡嗡作响地转了起来,听到机器声的那一刻,李建来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半块。
可生产恢复了,“活路”仍未找到。想贷款扩大生产?李建来带着财务科的人跑了好几家银行,人家一看企业的负债表,头摇得像拨浪鼓,直言“风险太大,批不了”;盼政策性破产?去省里问了好几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等”,可这“等”字,让人心里七上八下;想靠卖库存、收欠款维持?仓库里的旧纱不值一文,外地客户欠的款子催了又催,回收速度慢如蜗牛,那点钱如同杯水车薪,撑不了多久——再这么下去,迟早得“弹尽粮绝”。班子里开了好几次会,烟蒂堆了满满一烟灰缸,最后大家拧成一股绳,得出一个结论:企业要活下去,只剩一条路——找愿意“带资进入”的老板,搞租赁合作。
区政府给他们吃了定心丸:“先稳住阵脚,稳定局面,我们大家一起争取时间,找机会。”有了这句话,他们心里稍微踏实了点。只是谁也没料到,机会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是老领导任希平带来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任希平主任曾是洪纺的老厂长,对这片厂子情深义重,明白他们急着找出路,便四处托人打听。没过多久,他兴冲冲地来办公室找李建来,说道:“有消息了!佛山众力棉业有限公司的马老板,可能有兴趣,我已经跟他联系上了。”那天,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李建来能看到他眼里的光,那是柳暗花明的希望之光。
没过几天,马老板便来了。他叫马自强,个子高挑,身材挺拔,两眼炯炯有神,一看就是脚踏实地干实事的人。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与湖南的湘纺、常纺做了多年生意,是纺织行业里的“行家里手”。他带了几个人来,一进厂区就直奔车间,争分夺秒得没顾上喝口水:在梳棉机旁蹲了半天,盯着棉条看质量;到布机前查停台原因,问得事无巨细;连仓库里的库存纱都翻出来,用手摸了又摸,对着光看了又看,嘴里还念念有词,仿佛在盘算着什么,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考察了三天,马老板跟区领导坐下来商谈。他喝了口茶,缓缓说道:“洪纺虽比不了湘纺、常纺,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基础还在,职工也能吃苦。更重要的是,区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有诚意,这比啥都强。”没几天,好消息便传来了:他要跟区政府签租赁合同。听到消息的那天,李建来在车间走了一圈,看到工人们虽没说话,但脸上的愁云好像散了些,机器转得都比平时稳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绝境求生,总算看到了曙光。
签合同的时候,马老板特意跟区领导提了个请求:“为了企业稳定,我希望李总能到乙方来工作。我知道他一直在搞生产技术和管理,对洪纺的情况熟。”区领导当场表态:“这是好事!你把乙方的生产经营搞好了,稳定了,就是帮我们甲方做好了工作。李总在甲方的职务不免,政治待遇不变。”
就这样,李建来从“洪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变成了马老板这边的总经理(甲方的工作由唐三保接手)。他们还请了唐仲辉担任乙方的副总经理。2001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洪纺通过月底盘存,把纺织生产经营设施一五一十移交给了马老板在洪江注册的“洪江四海棉业有限公司”。第二天一早,四海棉业就启动了生产——没有停工,没有混乱,一线的干部职员们像往常一样上班,只是胸前的厂牌换了名字。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持续了半年多的“洪纺风波”,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平息了,真可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
四海棉业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层干部会上,马老板站在台上,语气很实在:“公司虽然成立了,但能不能搞好,不能靠天靠地,只能靠自己。”他特意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又说:“别总想着‘以前是企业的主人,现在是打工的’——这种想法不对。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扎实干,收入肯定比在国企时多!”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 。
他给企业定了新方针:“务实、应变,求强”。又明确了目标:“现在洪纺的纱布产质量,在省内中型企业里算不错,但跟‘八大棉’比,还差得远——他们早就全面达到行业一档水平了,我们还在二、三档徘徊。目标是:两年内,咱们的纱布产质量,必须全面达到一档水平!”他顿了顿,看着李建来说:“我把李总请过来,就是因为信得过大家。”
细纱车间的付兴盛主任当场站起来:“马总放心,提高产质量没有捷径,就是扎实干。我们车间肯定往前冲!”
那阵子,厂里的劲头真不一样。有天晚上九点多,李建来在办公的地方处理报表,唐仲飞推门进来,一边拍着身上的棉絮灰,一边说:“我刚转了转车间,主任们都还在机台旁呢。张玉林在看浆纱分绞的质量,生怕有一根纱绞错了;贺龙怡蹲在布机旁,盯着停台记录,跟挡车工说‘这台机的断经要重点查’;前纺的赵声江、方勇在梳棉间,拿着棉条跟标准样对比……”大家都在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实际做到了“上下同欲者胜” 。
李建来笑着说:“是呀,这两个多月变化真不小。但你得跟大家说,咱们要打‘持久战’,不是‘疲劳战’,该休息就得休息,劳逸结合才行。”
其实最让李建来感慨的,是民企和国企的不一样。以前在国企时,也喊“以用户为中心”,也说“抓质量”,但都是“纸上谈兵”,如同“隔靴搔痒”,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 。销售人员只要把货卖出去就行,用户反映质量上的问题了,要么反馈不回来,要么拖到最后“不了了之”。生产车间想抓质量,也只能“瞎抓”——不知道用户到底嫌哪里不好,只能笼统地“提高标准”,反而白费功夫,这就是典型的“盲人摸象”,不得要领 。
民企就不一样了。马老板亲自坐镇销售网点,天天跟客户打交道,市场上一点“风吹草动”,他当天就知道。为了让质量上的问题反馈更准,他还在销售网点建了“质量监测室”,配了专门的质量工程师,带着仪器随时走访客户。客户说“这批布的棉结多”,工程师当场取样、分析,当天就打电话跟生产厂的副总对接;月底还得回厂里一趟,带着客户的意见和解决方案,跟车间主任一条一条碰。
这样一来,生产上少走了太多弯路。比如梳棉车间,以前总琢磨“怎么提高棉条光洁度”,瞎试了不少方法,如同“没头的苍蝇”乱撞 ;后来质量工程师带回来消息:“客户最嫌的是‘棉结’,不是‘毛羽’”,车间立刻调整工艺,断头率降了,效率反而上去了。纺织这行就是这样:断头率低了,成本自然降,质量也跟着好——这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真是他们以前在国企时做得最不够的。
转眼到了2002年10月,四海棉业成立一周年的总结会。马老板站在台上,手里拿着报表,声音洪亮:“对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的纱布产质量,提前达到行业一档水平了!”台下的掌声“哗”地响起来,比机器的轰鸣声还震耳。马老板笑着说:“这掌声,属于我们自己!”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
任希平主任也来了,他站在台上说:“感谢大家这一年的辛苦。没有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洪纺的改制转型走不到今天。区里会一如既往地支持马老板,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三年后,马老板又在洪江投了钱,新盖了两栋厂房,纱锭从原来的3.5万锭扩到了5万锭。老洪纺没倒,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在曲折中发展壮大”的目标,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
后来李建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贵州。回洪江的次数少了,但心里总惦记着那片厂子。有次回去,特意绕到四海棉业,在龙总的办公室坐了坐(龙总是马老板的妻弟,后来负责厂里的日常管理)。王书华也在(他现在是洪纺的负责人),他们三个聊起当年的事,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龙总说:“那会儿在洪江能做成,一是职工们实在,肯干;二是区政府真支持——不管是政策还是协调,从来没含糊过。马老板就是看到这点,才下决心扩大投资的。”
李建来望着窗外的厂房,心里叹口气:是啊,真是缘分。当年要是没任希平主任牵线,没马老板敢闯敢干,没区政府兜底,洪纺说不定就真散了。自己能赶上这段日子,跟着厂子从“风雨飘摇”走到“柳暗花明”,虽然熬了不少夜、掉了不少头发,可看着机器转得越来越欢,职工们的工资袋越来越鼓,就觉得值了。有些事,经历过,就是一辈子的念想。正如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段经历也将成为大家心中最宝贵的财富 。
听了王书华主任的口述后,我非常之激动。洪纺从78年底投产,经历了22年,走向了破产抵债,马老板又租赁了22年,使洪纺起死回生。一举三得的合作,一是市里得到产值,税费,二是马老板早几年赚得盆滿钵满,三是熬得职工获得圆满的退休保障。这里有区委区政府的良苦用心,有马老板的苦心经营,有全厂职工忍辱负重,才共筑了这一“三得利”的创举,收获了皆大欢喜的圆满成功。
2001年的洪江纺织厂,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彼时,这家曾是区域经济龙头的企业,已被600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企业办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专职消防队,经警队、职工医院、幼儿园,子弟学校,招待所等机构年耗费巨大)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冲击压得喘不过气。产品单一、设备老化,连基本的生产运转都难以为继,这年4月,工厂正式宣告破产,欲死而复活。
破产后的日子里,两千名职工的安置成了最大难题。政府财政拮据,企业固定资产无法变现,职工身份置换迟迟不能推进,社保、医保的缴纳缺口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就在这时,曾任洪纺厂长的后任洪江区政协主席任希平和管工业的印告成主任一边搞破产,一边想办法,既要保住洪纺的产值,税费,又要保住职工的饭碗,还要保住老职工的退休保障。他们想起了一个人——佛山商人马自强。马老板此前曾为我厂销过产品,对工厂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且具备一定实力。为了给职工找一条出路,任希平和印吉成多次带队前往广东佛山,与马老板沟通协商,从工厂现状到职工诉求,从租赁细节到未来规划,反复考察、磨合。
终于2001年9月13日,双方原达成协议:马老板以xxxx万元意向金整体收购纺织厂,但因职工身份置换需1.7亿元的巨额资金,最终转为租赁形式,每月支付20一一23万元不等的租赁费,用于破产留守人员运转和职工基本养老上缴费用。
马老板接管后,将工厂更名为金丰公司旗下四海棉业分公司,首先甩掉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压缩了众多的管理人员,轻装上阵,不仅保留了大部分原职工,还投入真金白银做改造:技改方面,修建了2000多平米的框架式厂房,置换了400多台布机,购量了意大利和德国的自动络筒机,和新型抓棉机和清刚联梳棉併条机。大约投入7000来万元。
租赁后除了总经理,财务和原料采购,从副总经理到部车间主任,各部室部,均由洪纺原职工担任。他聘请了我方的李建来,唐仲飞,付兴盛,邹之辉等熟悉纺织行业的中高层骨干,试图用专业管理盘活这家老厂。
最初的几年,租赁模式确实带来了生机。当时职工人均工资约500元/月,用工成本相比来说较低,工厂利润尚可,年均向政府缴纳相关税费约500万元左右,每年200多万元的租赁费,成了职工社保、医保和下岗工资的“救命钱”。那些年,走进厂区,还能看到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听到职工们熟悉的交流声,不少人均为“老纺织厂又活过来了”而欢心鼓舞。
2023年6月,在坚持了数年之后,马老板终究没能扛住持续的亏损,工厂正式关闭。尽管租赁的结局是停产关门,但这二十余年里,马老板的接管像一根“救命稻草”——它让上千名职工有了就业岗位,让社保、医保的缴纳得以维系,更让无数家庭在转型的阵痛中,多了一份喘息的空间。
洪江纺织厂曾是当地的“顶梁柱”,鼎盛时期,其产值在区域内占了半壁江山,养活了数千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庭。然而,当计划经济的光环褪去,工厂破产后的职工安置问题,成了政府必须扛起来的责任。从破产初期到如今大部分职工平稳退休,政府的每一步施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绝不能让职工因‘’断了后路。”
破产之初,职工最担心的是“身份没了,保障也没了”。2005年,部分职工在黄大毛等人的带领下,希望能够通过“”一次性处理问题,工厂甚至因此停产半个月。面对这场风波,政府没有回避,而是明确承诺:“退休职工全部纳入职工医保,社保、医保的差额缺口,由财政兜底。”这一句承诺,背后是巨大的压力——当时政府财政并不宽裕,仅社保、医保的年垫付额,在2014-2016年的高峰期就达1100万-1400万元,省社保挂账一度高达2000多万元,连滞纳金都快超过本金。但政府没有退缩,一边向上争取政策,多次到省社保协调减免滞纳金、延缓还款;一边统筹区域资金,哪怕压缩其他开支,也要先保障职工的社保、医保缴纳。
为了让职工“熬到退休”,政府还想出了“以租养企、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引入马老板租赁经营,正是这一思路的关键。每年,区里分管工业的区长(如罗国贵等)都会带队与马老板协商租赁细节,确保租赁费按时到账。这些资金像“输血管”,源源不断地流向职工的社保账户、医保账户,以及下岗职工的工资卡上。从2001年移交时的2000多名未退休职工,到如今仅剩420人,正是靠着这二十几年的“过渡”,大部分职工一步步走到了退休的节点。
政府的良苦用心,还藏在许多细节里。针对退休职工的医保问题,政府与医保局反复协商,争取到“退休后补交个人部分、边交边享受待遇”的灵活政策,避免职工因一次性缴不清费用而失去医疗保障。对于女性职工,明确按企业职工身份50岁退休,而非灵活就业人员的55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她们能早5年领取养老金,少缴5年社保,背后是数十万的切身利益。此外,政府最近还推进了纺织厂区域的旧房改造,曾经老旧的职工宿舍焕然一新,航拍镜头里,整齐的楼房、整洁的街道,成了职工生活环境改善的最好证明。
如今,尽管工厂已停产,但看着大部分同事顺利退休,拿着养老金、享受着职工医保,纺织厂的老职工们心里清楚:这背后,是政府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不放弃任何一个职工,不让任何一个家庭在时代的转型中掉队。马老板的二十多年的租赁,是市场力量在特殊时期的一次托举,而政府的持续护航,则是社会保障体系在转型阵痛中的温情落地。二者的接力,让洪江纺织厂的职工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既感受到了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凛冽,也触摸到了政策兜底的温暖,为同类老工业企业的职工安置,留下了一段值得回望的实践样本。
我有几个安纺的朋友说,他们当时破产后,被政府把身份买断,每人打发了几千元,自已交社保医保,多数职因病提前退休,导致职工退休工资少之又少。还是你们洪纺好,政府多措并举,把职工掌起了退休保障的保护伞。
那段从国企到私企的转型岁月,曾让每一位洪纺底层职工在阵痛中品味过无奈,但风雨终会过去。如今回望,这家企业的涅槃是否真正圆满,或许就藏在每一位洪纺人安稳的退休时光里——那是岁月给奋斗者最实在的答案。
从李建来、唐三保到王书华,一代代掌舵人接力守护,不管法人代表的名字如何更迭,这里始终是刻着“洪纺”二字的家。如今大门虽暂闭,寂静中却满是四十余载的故事沉淀:车间里机器的轰鸣、食堂飘出的饭菜香、交接班时的一句寒暄,都藏在这方天地里。
洪纺的老伙计们,常回来看看吧!这扇门里封存的不只是时光,更是咱一起用青春酿出的酸甜苦辣。那些日子从未远去,它们在记忆里发烫,等着咱们再聚时,笑着数算当年的故事,让这份洪纺情,永远热热闹闹!